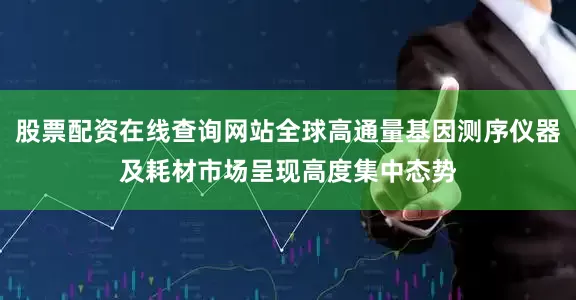以前的我,是一个“没长性”的人。
这是我母亲的评价。
它像一道诅咒,深深刻进我的骨髓。
我不停地自我否定,一次次放弃,仿佛只为证明它。
我的前20余年,都活成母亲口中那个“什么都坚持不下去”的人。
直到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,我才惊觉:
有些枷锁,不挣脱,就会代代相传。
今天,我分享出自己的经历,想告诉你:
真正的成长,始于你不再为上一代的创伤买单。

我的痛苦“遗传”到了女儿身上
在大一时,我就有明显的痛苦感了。
因为高考失利,我暗自发誓,一定要考好成绩“一雪前耻”。
可我的脑海中总有一个声音:“你怎么努力都没用,注定一事无成。”
在这个声音的“蛊惑”下,我一边心里想要学习,一边却学不进去。
每天逼自己去自习,学习过程中却总在发呆;
跟室友约好早起跑步再去自习,结果没坚持几天就退出约定。
我的每一个举动,似乎都在验证母亲的“预言”:我就是一个“没长性”的人。
我隐隐觉得,自己需要接受心理咨询。
可对当时在五六线小城市,出身于底层工人家庭的我来说,这种在一线城市才有的,价格不菲的心理服务,我根本承担不起。
于是,我“背”着这些痛苦,苟且前行了20余年。
我以为,随着时间流逝,痛苦会逐渐淡掉。
直到女儿上了小学——我发现她极其苛责、看低自己。
给她讲题的1个小时,我只用5分钟讲题,剩下55分钟都在安抚她愤怒又讨厌自己的情绪。
当她哭喊着:“我就是笨!我怎么都学不会!”时,我像被回旋镖击中:
看见了20年前,那个蜷缩在书桌前,泪流不止的小女孩。

我意识到,如果我不做点什么,女儿很可能会走上和我相似的路:
在自我否定中挣扎,在他人的评价里寻找存在感,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一生。
那一刻,为了女儿,也为了我自己。
我打开了预约心理咨询的平台,为自己安排了在20年前就想开始的咨询。

我的焦虑不是自己长出来的
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,我紧张得手心冒汗,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咨询师L安静地坐在我对面,没有评判,只是轻声说:“慢慢来,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我满腹的委屈似乎终于找到了出口,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哭得无法自抑。
情绪稍稍平复后,我开口:“我女儿总觉得自己不够好,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”
L没有直接教我怎么做,而是问我:“你说女儿觉得自己不够好,能具体说说有哪些表现吗?”
我开始描述女儿如何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否定自己、如何不敢尝试新事物、如何总是寻求我的认可……
说着说着,我又开始哽咽:“其实这些……这些我都经历过。”
L:“听起来,你似乎在自己女儿身上看到了某些熟悉的模式?”
那一刻,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:
我的女儿正在重演我的童年剧本。而这个剧本,是由我的母亲“写”下的。
比如我的焦虑。
每个交到我手里的工作,从接到它的第一时间,到完成它交付后,我都深陷在焦虑中。
只有在交付得到肯定的那一刹那,我才能稍微得到片刻的安宁。
但其实,我的领导很信任也很欣赏我的能力,我也确信自己交付的结果是会让领导满意的。
可为什么,我始终会在最终交付前惶惶不可终日呢?

咨询里,L引导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。
通过把那些经历“掏”出来,反复拆解和讨论,我发现:
我的母亲就是那种“心中装不了任何事的人”。
不到事情结束,有个最终结果,她就会惶惶不可终日,没法让自己有片刻轻松。
比如之前,她过来帮忙带娃的时候。
只要女儿有点着凉、鼻子堵,母亲就总一脸愁容。
直到女儿好了,她的焦虑才会稍许驱散。
然后,在女儿的恢复过程中,她会不断埋怨:
“我就说要给娃多穿一件衣服吧,你偏不!”“就说别去泡温泉,你看,孩子感冒了吧!”“就是你不听我的!听我的,孩子就不会感冒了!”
我试图反驳:“妈,孩子感冒也是免疫力升级的过程,挺正常的。谁还不感个冒、发个烧啊。”
可母亲的回应仍旧是:愁眉不展、满腹牢骚。
而这时,原本比较淡定的我,就也会生出无限的自责与愤怒。
原来,我的焦虑,是在耳濡目染了母亲的焦虑后“学”来的。
很神奇,意识到这点之后,我紧绷的神经开始变得松弛了。

看见代际传递的创伤
后来,随着咨询深入,更深的共生关系浮出水面。
我发现,自己早已习惯成为母亲的情绪容器。
母亲像八爪鱼一样,把我勒得紧紧的。我明明都快窒息了,却依然在安抚她的情绪。
她打来电话抱怨父亲时,我会绞尽脑汁地安慰、陪着骂;
她情绪低落,我也会很焦虑,好像必须得驱散她的乌云。

L点出:“你把妈妈的感受当成了自己的责任,她的情绪成了你情绪的遥控器。这种纠缠,心理学上称为‘共生’。”
接着,又问我:“可你真的需要为所有人的情绪负责吗?”
这个问题直击我的灵魂。
是啊,我为什么这么痛苦?
原因之一就是,我需要对所有人的情绪负责,尤其是我的父母。
我想拯救所有人的情绪,让所有人开心,却唯独忽略了自己。
难怪我总是那么疲惫,只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有片刻的轻松。
因为那时,所有人都睡了,我终于能为自己活一会儿了。
咨询里,L让我尝试一种特别的练习:
她让我想象母亲就坐在对面的空椅子上,让我把想说的话直接“告诉”她。
一开始,我手足无措。
L鼓励我:“试着把心里那些没说出的话说出来,喊出来也行。”
“妈!”我对着空椅子,声音嘶哑,“我真的好累!你的不开心为什么都要我承担?”
这句话像打开了一道闸门,二十年的委屈、愤怒、无助喷涌而出。
我泣不成声,身体剧烈颤抖,但又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L就那样静静地陪伴着,直到我宣泄完毕。
那次之后,一种奇异的轻松感从我心底升起。
我意识到:
母亲的痛苦是她的人生课题,不是我必须背负的十字架。
接着,我开始和L一同探索“母女关系”这一课题。
L引导我思考:母亲的焦虑,对我的苛责,是否也源于她的成长创伤?

答案是肯定的。
母亲是家里的老大,外公对她的控制欲尤其强。
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大女儿反驳自己的意见。
即便是母亲的终身大事,都是由外公一人独断,从没考虑过母亲的感受。
而母亲对待我的方式,几乎是外公对待她的翻版。
那些苛责,是她内化了的外公的声音;那份焦虑,是她未能摆脱的枷锁,传递到了我身上。
“代际传递的创伤,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死结,”L说,“上一代未能处理好的痛苦,常常会无意识地塞给下一代。看见它,是解开它的第一步。”
这次探索的启发,改变了我很多。
我对母亲有了更深层的心疼,那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悲鸣。
同时,我也意识到,要斩断这种“传承”:
把属于母亲的课题还给她,把属于我的人生拿回来。

我只需为自己的人生负责
“看见”之后,就是行动。
我在L的建议下,开始尝试建立边界。
先从小事开始:
当母亲说“你这件衣服太老气了”,我会反驳“我觉得穿着舒服就行”;
当她探究“你老公这个月工资发了多少”,我会说“够我们花,具体就不跟你说了”。
当她又一次说“你要是当初听我的……”,我不再沉默不语,而是反击:“我不是小孩子了,我需要自己的空间,我不喜欢你干预我。”
母亲愣了一下,没再说话。
之后,她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联系我。
我也借此逐渐完成与原生家庭物理意义上的切割,并开始精神上的切割。
这种“切割”,不是断绝关系,而是划清健康的界限,各自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
这过程伴随着阵痛与反复的内疚,但那个痛苦了20年的我,也正在一点点地挣脱枷锁。

更惊喜的是,女儿随着我的改变也在改变。
她写作业时不再因一道题而崩溃大哭。
有一天,她居然拿着老师批改后的一道题来问我:“妈妈,我觉得老师这题改得不对,你看……”
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思路。
那一刻,我眼眶发热——女儿在挑战“权威”,她在勇敢地说出“我认为”。
这正是我曾经最缺乏的力量。
回望这段路,我常想:
如果20年前,我就有勇气推开那扇咨询室的门,我的人生会少多少无谓的消耗?
咨询不是魔法,它无法一键清除过往的伤痛。
但它提供了一面镜子,让你看清伤痛的模样和根源,自己生出的力量去改变。
我无法改写自己童年,但我还有机会改写女儿的童年。
当我学会在母亲情绪的风暴中稳住自己,女儿便不再被卷入其中;
当我停止苛责自己,女儿也不再自我苛责。
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,终将成为孩子最初的生命语言。
如果,你也在自我否定的循环里挣扎;也发现自己在无意识地重复父母的模式;想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成长环境……
那么,找个咨询师聊聊吧。
毕竟,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,不是为了重复上一代人的人生,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一生。
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咨询师,可以看看这位经验丰富、专业扎实的咨询师——李雪。
李雪老师是国家二级咨询师、儿童心理成长指导师、情绪管理师,从业超15年,积累个案时长5800+小时。
李老师在个人成长、童年创伤、抑郁焦虑等议题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同时她会以认知行为疗法、心理动力取向、人本主义取向等方法,根据来访者的具体情况灵活制定咨询方案。
为鼓励求助意愿,李老师特地开通了3个半价咨询名额,原价700元/次的咨询,现仅350元。
↓给自己一次走出创伤的机会↓
如果,你也有被过分控制、被情感忽视、被亲子反转等未愈合的童年创伤,又想选择更多不同风格的咨询师,不妨试试壹心理的「半价咨询」,找到更合适你的那一位咨询师↓
作者:来访者暖阳
编辑:小西
图源:图虫创意、Unsplash
华泰优配-华泰优配官网-个人股票配资-线上股票配资门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